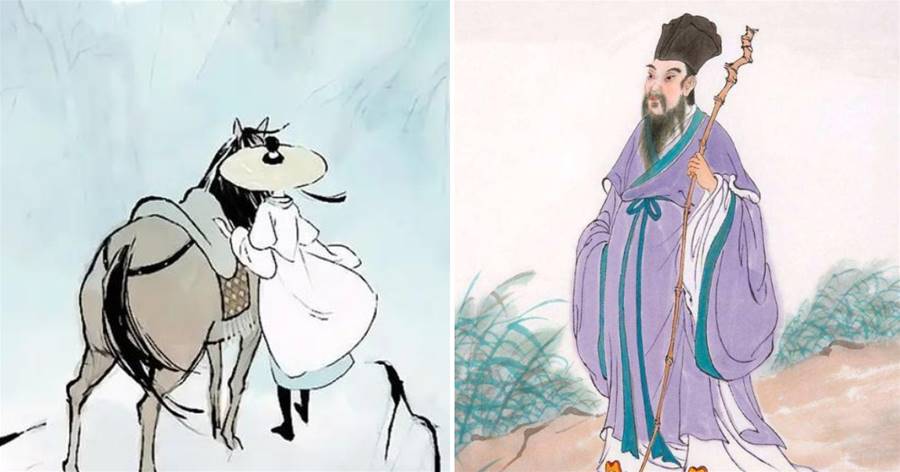


01 | 認知
人類的悲歡各不相通。
不同層次的人對苦難的感知,存在著一定的排異和費解。
比如說,一個普通人丟了10000塊錢,會覺得很心疼、很心疼,對更加拮據的家庭而言,甚至是一個沉痛的打擊。
但是對于一個被騙子騙了10萬元的,更高階層的人而言,他可能會很慶幸:唉,幸好發現得早,剩下的100萬保住了。
所以很多人質疑,蘇東坡一生為官,大部分都是任知州,除了被貶黃州謫團練副使外,最低官職也是判官,相當于中央駐派到地方的廳級干部,他何苦之有呢?
況且,除了發妻王弗,他還娶了其胞妹王閏之,以及愛妾朝云。
但如果你詳細了解了蘇東坡這一生,或許你就不會這樣認為了。
就像凱撒大帝的孤獨,是最后站在古羅馬城墻上端倪天下,發現再也沒有了對手。

02 | 起伏
那年蘇東坡20歲,第一次隨父來到京城,花花世界,看什麼都好。
次一年,他參加了會試,當時的主考官是歐陽修,小試官是梅堯臣,皆是文壇領袖,正在醞釀著詩文改革。
試后,梅堯臣發現了一篇奇文,題為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,極力推崇,于是就拿給了歐陽修過目。
歐陽修讀后很詫異,連問了梅堯臣幾遍:文中典故出自何處?
梅堯臣搖頭,作答:文采飛揚,何必知道出處呢!
歐陽修不死心,回家查了一夜古籍,還是沒有找到典源,然后仔細想了想這代青年才俊中的佼佼者,認為該是自己學生曾鞏之作,所以為了避嫌,就判了第二名。
放榜拆名時,歐陽修和梅堯臣才知道,原來這是蘇家蘇軾的考卷,遂大加贊揚,并揚言:此子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。
可歐陽修不死心,在蘇東坡登門謁謝時,又一次問了文章中的典故,蘇東坡借用了孔融「想當然」之意,頗為豪放地說,又何必有出處呢!
這一言論與梅堯臣不謀而合,所以從那以后,歐陽修對蘇東坡總是另眼相待。

可就在蘇東坡要擼胳膊、挽袖子大干一場時,眉州傳來噩訊,蘇母病逝。
于是,蘇東坡與弟蘇轍歸鄉守孝三年。
人要倒霉,喝涼水有時候都會塞牙。
三年后,蘇東坡還京,而蘇轍則授澠池縣主簿,所以分別時蘇東坡有詩相贈:
人生到處知何似,應似飛鴻踏雪泥。
泥上偶然留指爪,鴻飛那復計東西。
從人生境界上來看,這個年紀的蘇東坡已經心懷若谷,所以當時朝中幾乎所有官員都認為,這是天之驕子,將來必定指點江山。
更加厲害的是,蘇東坡授官前還須參加一次制科考試,但他得了百年第一,于是授鳳翔府簽判,一起跟隨的還有他的學生(亦師亦友)董傳。
「桃李滿門」原本是形容狄仁杰的,但是「蘇門學子」真可謂是遍布四海,而此時的蘇東坡才剛剛24歲。

三年后,董傳學成欲歸京參加科舉,離別時蘇東坡有言相贈:
粗繒大布裹生涯,腹有詩書氣自華。
厭伴老儒烹瓠葉,強隨舉子踏槐花。
董傳離后,蘇東坡任期將滿,也準備還朝了。
公元1065年,28歲的蘇東坡授任判登聞鼓院、充直史館,可他的仕途之路才剛起頭,父親蘇洵也過世了。
于是,蘇家兄弟扶柩還鄉,再次守孝三年。
還有更加讓他悲傷的是,此間他的愛妻王弗也因病不治,與世長辭了,芳年27歲。
一晃,蘇東坡就過了而立之年。
再回朝時,朝局風云突變,王安石開始推行變法,因政見不合,蘇東坡上書論述新法弊端,王安石非常生氣,便指使御史謝景在神宗面前談論蘇東坡過失。
無奈之下,蘇東坡自請出朝,任杭州通判,那一年是公元1071年。

往后的事,如果要敘述詳盡,恐怕得說上三天三夜,總之自此以后,蘇東坡開始了顛沛流離的一生,直到終老。
我們就簡單說一下他都在哪里做過官吧。
1074年,蘇東坡知密州,依舊是三年任期,后赴徐州治水,兩年后「烏台詩案」爆發,遂貶黃州。
1084年,蘇東坡收到調令,復命汝州,途中痛失幼子,故辭官留在了常州。
1085年,神宗駕崩,司馬光復相,蘇東坡知登州,四個月后還朝,回到了開封,擢起居舍人、后接連升任中書舍人、翰林學士、知制誥,知禮部貢舉。
四年后,蘇東坡厭倦了朝內「黨爭」,再次自請出朝,回到了杭州任知州,然而好景不長,兩年后蘇東坡又被調往潁州任知州,隨后是揚州、定州、寧遠,最后被一葉扁舟送到了儋州。
儋州留下不朽功業后,蘇東坡被調廉州、舒州、永州,此時他已經進入了人生末年,朝廷大赦,復朝散郎,并準其致仕歸田。
一年后,64歲的蘇東坡在常州安逝,走完了自己飄搖動蕩、顛沛流離的一生。
做官,他是不成功的,從來沒在一個任上超過四年,而且多數都是被貶走,「烏台詩案」還差點讓他掉了腦袋。
但若是沒有這些經歷,我們可能也看不到「千古第一詞帝」的誕生了。
這一切,都要感謝黃州那四年的艱苦日子。

03 | 蛻變
在蘇東坡反對王安石變法后,新黨成員就記下了這筆仇。
熙寧六年,公元1073年,王安石的門生沈括偶然間得到一首蘇東坡的詩,認為有誹謗朝廷之意,便以檢正中書刑房公事的身份上奏給了宋神宗,當時神宗并未理會。
六年后,以舒亶、何正臣、李定為首的御史台,學會了沈括這招,于是卷土重來,把蘇東坡的詩詞翻了個遍,然后輪番彈劾,最終將蘇東坡收入御史台大獄。
當時羅織的罪名是:愚弄朝廷、妄自尊大、銜怨懷怒、指斥乘輿、包藏禍心,諷刺朝政,莽撞無禮,對皇帝不忠……總之,就是想讓他死。
況,前又有《湖州謝表》「愚不適時,難以追陪新進、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」之句,所以這一次神宗怒了。

實際上,此時的王安石已經致仕,回到金陵養老了,作為一代「文宗」,他還是明事理的,畢竟宰相肚子能撐船,于是他上書神宗,直言: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?
就這樣,轟動一時的烏台詩案因王安石一言而決,蘇東坡被貶黃州任團練副使,并受朝廷監查。
所以黃州四年,蘇東坡一直過得很苦,連生計都是問題,故自己開荒墾田,取號「東坡居士」。
磨難往往也能帶來改變,正是這四年的困苦,才讓蘇東坡重新審視了人生,比如在《定風波》中他寫:竹杖芒鞋輕勝馬,誰怕?一蓑煙雨任平生。
在《臨江仙》中他又寫:小舟從此逝,江海寄余生。
在那里,蘇東坡還完成了絕唱千古的「一詞兩賦」,開創了一代詞賦之新風。

于是,他也漸漸理解了王安石,公元1084年他出黃州后,還刻意去看望了王安石,一笑泯恩仇,并約好了將來一起養老。
遺憾的是,赴汝州途中,他和朝云剛剛出生的孩子夭折了,心灰意冷之下,蘇東坡決定辭官在常州養老,悉心陪伴家人。
期間蘇東坡曾和好友參寥共游廬山,紓解心情,在那里他寫下了一首《題西林壁》:
橫看成嶺側成峰,遠近高低各不同。
不識廬山真面目,只緣身在此山中。
這是蘇東坡凝聚了所有智慧,在經歷浮世萬千后,所作的一首哲理性很深的詩。
曾經有人說過,蘇東坡擅詞,詩顯弱。
猶記得李白登廬山,寫下《望廬山瀑布》后,亦有時人言,以后不會再有人敢寫廬山了,畢竟前有李白登黃鶴樓為崔顥擱筆一事。
未曾想,幾百年過去了,蘇東坡不但寫了廬山,還寫得毫不遜色。

蘇東坡這首詩,美在意上,深在哲里。
人的一生就是個迷局,身處其中,往往很難看透,有時候,你真的需要跳出自己所在的圈子,才能以窺全貌。
然后發現自己的不足和欠缺。
比如有人貪財、貪名、貪權,覺得擁有財富和力量就能擁有一生,可在另一些人平凡人眼里,會覺得他們活得很累,處處都處心積慮,生怕哪一步走錯了就是萬丈深淵。
等有一天,他們暮年之時再回頭望一望曾經的你爭我奪,也會發現很無聊。
所以,讀懂了蘇東坡這首詩,也就讀懂了一個人的一生。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