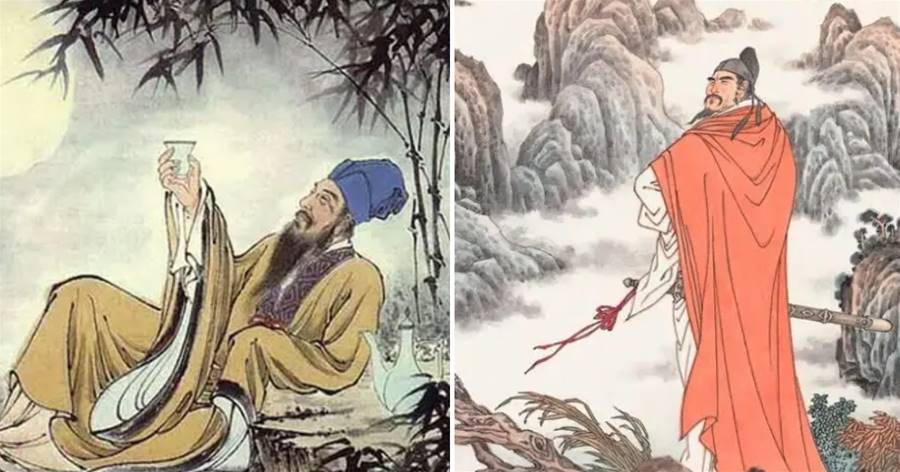

現代人常說喜歡一個人:始于顏值,敬于才華,終于人品。
而在文學上,對于人最直接的喜愛,則是他的才華。
年代久遠,或不清楚歷史中對方的經歷,便不會去追究其品性,唯有真正喜愛,才會想著去研究一下詩人的歷程。

而在這其中,不少剛開始覺得才華橫溢的詩人,最后發現卻有幾分污濁不堪,白瞎了些好詩詞。而有些的詩人則是越讀越愛,他的詩詞,他的人生,他的品性,無不廣受敬仰。
其中的佼佼者自然離不開蘇·美食家·治水專家·弟控狂魔·吃貨·越貶越遠·永遠在路上·想起他就會心一笑的·東坡,還有總被人拿出來與他一較高下的辛·硬核狠人·超能打·大宋第一猛人·能文能武·如果不把名字連在一起就很難用拼音打出的·棄疾。
今日,便看一看這兩位詞人在醉酒后寫出的詩詞,藏著怎樣有趣的人格吧。

壹
在寫蘇軾之前,我總忍不住想到李白,不由得感想,唯有盛世中,才能誕生如此狂放不羈的人才,李白是,蘇東坡也是。
一個好的社會環境,對人產生的影響是不一樣的,當然這也有個人性格相關的東西。
但我總覺得李白與蘇軾,似乎和國家的繁華強盛是離不開的。
李白的詩,總有幾分大唐盛世的深入骨髓的自信,甚至是狂傲之氣,而蘇軾的詞,也離不開宋朝中期的富貴閑適。
唯有國家之強盛,詩人們的作品才不會狹隘,拘泥,困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。而個人的時局動蕩,不過看個人心態品性而已。
古人言:「言為心聲,文如其人」。
蘇軾的詞,也無一不透露著自己的品性格調,一首醉后的《臨江仙·夜歸臨皋》,寬厚且闊達。
夜飲東坡醒復醉,歸來仿佛三更。家童鼻息已雷鳴。敲門都不應,倚杖聽江聲。
長恨此身非我有,何時忘卻營營。夜闌風靜縠紋平。小舟從此逝,江海寄余生。
這首詞創作為神宗元豐五年(公元1082年)九月,這是他剛因為烏台詩案謫貶黃州不久。
上片主要是寫關于醉酒后的記憶,「夜飲東坡醒復醉,歸來仿佛三更」,剛喝酒,還醉醺醺的,頭腦有些不太清楚,依稀感覺是到家的時間是夜半三更,因為這首詞是酒醒后所作,蘇仙有點喝斷片了。接下來繼續回憶到家之后的事情,因為太晚了,家里的小仆人都睡著了,鼾聲如雷,怎麼敲都不醒,哎,那能怎麼辦了,「倚仗聽江聲」。沒有不止不休的敲門,而是自己一個人默默地聽著外面滔滔的江水聲。行文至此,一個豪醉疏狂,又歸家不得入,黯然無措又樂觀豁達的人物形象躍然于紙上。
比樂觀豁達更為重要的寬厚人品,隱藏在上片的細節中。家里書童早早睡下了,主人敲門也沒有聽到,沒有及時出來開門,按一般人早已暴跳如雷,而蘇仙卻很能理解,沒有發酒瘋,哐哐砸門,順便把書童教訓一頓,反而寫出一種長輩的寬厚,且讓他再睡會吧,我聽聽江水聲,等下可能他就醒了。
下片便是抒發自己的感想,「長恨此身非我有,何時忘卻營營」出自《莊子·知北游》「汝生非汝有也」,這人生總是生不由己,何日才能不汲汲營營,追逐于名利?
這奇峰突起的喟嘆,是全詞轉折的樞紐,從平平無奇的日常一百八十度轉變為對人生的哲思,關于哲學的拷問。
情之所至,興致而起,瀟灑豪放,非蘇軾不能也。宋人評價「居士橫放杰出,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」。
夜晚靜悄悄的,微風不起,江面上也是一片風平浪靜,一時間只覺得天地寧靜,遼闊而包容,蘇仙在寧靜而美麗的夜晚被自然所陶醉,心下一派澄明,不由得生出幾分遐想:我且放下這俗世功名,乘一葉扁舟,寄情于山水吧,將有限的生命融入廣袤無限的自然之中去吧。
「小舟從此逝,江海寄余生」。這一句韻味無窮,既表達蘇仙瀟灑如仙的曠達襟懷,又有幾分對世事的黯淡,所產生的傷感不滿,向往自由的心聲。
林語堂先生在他的著作《蘇東坡傳》中說:「像蘇東坡這樣的人物是世間不可無一難能有二的。對于這種人的人品個性做解釋,一般而論,總是徒勞無功的。」
一個偉大的詩人,人品與個性總是復雜的,而從詩詞中,你總能讀出不一樣的蘇東坡。
我見到蘇仙的寬厚,豁達與落寞;你見到蘇仙的瀟灑,曠達與樂觀。
但我們都不能否認的則是蘇仙所流露的一種達觀的人生態度,一種超曠的精神世界,一種獨特的個性和真性情。

貳
如果說蘇東坡是一個寬厚闊達的長者,而辛棄疾,則給人一種很爺們的神態。
他是一個飽經風霜的男人,一個心懷天下,又不免柔情的男人,一個成熟且富有魅力的男人。
他極少見婉約柔媚之氣,字里行間全是屬于一個心懷天下的男人的志氣。
而他醉后之情態,也是一個純純憨憨鋼鐵直男會做出來的事情,以至于似乎看到我們常見的醉漢。
可他不是癡兒愚夫,他只是有太多的不得已。
《西江月·遣興》
醉里且貪歡笑,要愁那得工夫。近來始覺古人書,信著全無是處。
昨夜松邊醉倒,問松我醉何如。只疑松動要來扶,以手推松曰去。
慶元年間(1195年—1201年2月5日)辛棄疾閑居瓢泉,南宋早已不思進取,沉迷最后虛假的的富貴榮華之中。辛棄疾面對局勢,深感無能為力,不免心情郁郁,喝酒解愁。
上片說在醉夢中放聲歡笑吧,哪里有那麼多功夫整日發愁呢。這其實算是一句反話,只因為清楚時期有太多難以言說的酸澀,只能大醉一場,獲得片刻歡愉。接下來又發出一聲感嘆,說我近來覺得古人圣賢書并不可信,讀了也沒有什麼用途。是這個意思嗎?其實不是。孟子曾說:「盡信書,則不如無書。」如果你全部相信書上所說,脫離社會現實,那你讀的書并沒有什麼用,因為它不僅不能帶給你知識反而讓你更加無知。
辛棄疾想表達的是,天下讀書人都是讀過圣賢書的人,更不論朝中大臣,大多是進士出身,可既然讀過書,又怎能不知廉恥,不事忠君報國,不為自己的國家與民眾做一番努力呢。
靖康恥,猶未雪,臣子恨,何時滅?
有這樣一群朝臣,和軟弱的帝王,圣賢之書,讀來何用?令人不勝唏噓。
下片則寫關于昨天醉酒后的回憶。「昨夜松邊醉倒,問松我醉何如。」直將松樹當成人,告訴它我沒醉,我才沒醉。這已不是微醺,而是大醉了,有些迷迷糊糊,人樹不分,倒在松樹邊,自己扶著松樹爬起來,還以為是朋友在攙扶自己,直接推了松樹一把,說:去。走開,不要你扶,我還沒醉。
讀至此處,忍不住會心一笑。一個醉醺醺又倔的醉漢形象躍然于紙上。
「以手推松曰去」,這是散文的句法。以前的宋詞多注重音律,追求婉轉,以求應和歌姬的歌喉,達到演唱的目的,而辛棄疾對于宋詞的寫作,則刨去了關于音律婉約的需求,將宋詞提拔到一個新的高度,不再是流傳于大街小巷的靡靡之音,而是可以抒寫抱負,更平易清新,更具格調的一種體裁。
這首詞平易簡白,如同白話,形似日記,文字生動活潑,手法新穎出奇,體現了作者晚年清麗淡雅的風格。
而我們不止讀到他的風趣可愛,也讀懂他難以言說的落寞與孤獨。

叁
時代與個人的修行造就了宋朝兩位并肩而立的文豪,其實更合適加上李清照,是三足鼎立的局面。
李清照那首名作《如夢令·常記溪亭日暮》:常記溪亭日暮,沉醉不知歸路。興盡晚回舟,誤入藕花深處。爭渡,爭渡,驚起一灘鷗鷺。
這首詞行文流暢,猶如清水芙蓉,不事雕琢,富有自然之美。
一樣體現了李清照蕭蕭肅肅,爽朗清舉的林下之風,其精神與格調與竹林七賢并齊,灑脫俊逸如陶淵明。
他們三人,也處在宋朝不同的時間段,蘇軾在北宋國力強盛,天下太平的時候;李清照則是北宋與南宋的過渡段,她經歷最后的繁榮,又經歷戰亂苦痛的,她的詩詞承載著人世變換與世事興衰;而辛棄疾則是戰亂末期,在一個充滿著恥辱,文人們猶有血性的時期,奈何皇室不作為,主和派偏大多數,眼見山河日下,王公大臣還沉迷最后的榮華,有志者有心無力,實在讓人絕望。
三首醉后之作,蘇軾的曠達悠遠,辛棄疾的沉郁生動,李清照的清新淡雅,風格迥異,各有格調,充分體現了三位文豪的才情與品性。
宋朝,若是沒有這三位文豪,則會平庸太多了。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