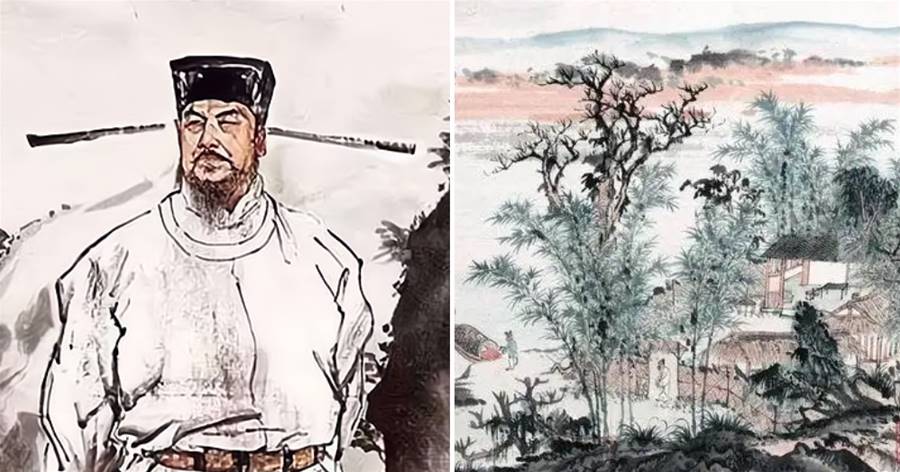

在眾多的古詩詞中,那些富有意境、畫面感極強的作品,往往更能博得讀者的喜歡。
宿建德江
移舟泊煙渚,日暮客愁新。
野曠天低樹,江清月近人。
比如唐代大詩人孟浩然的這首《宿建德江》,就以簡練的語言,將一幅清冷空曠的畫面臨摹出來,此詩能夠讓讀者在置身于畫境的同時,充分地感受到一位孤獨詩人的深沉客愁。可以說,這首詩能夠成為千古名篇,絕不是因為詩家的「強捧」,而是因為它「詩畫合一」的魅力;所以,能被讀者喜歡,才是王道。

追逐詩詞,細品人生;詩巷在本期要跟大家分享的,也是一首頗富畫境的詩。這首詩來自宋朝一位不知真實姓名的詩人,它有著《宿建德江》的幾番風韻,而且每一句都寫得十分生動,值得我們細細品讀。
泊白沙渡
宋·真山民
日暮片帆落,渡頭生暝煙。
與鷗分渚泊,邀月共船眠。
燈影漁舟外,湍聲客枕邊。
離懷正無奈,況復聽啼鵑。
真山民,真實姓名不詳。據記載,作者曾經自呼「山民」,而「真」,則是由人們推斷而來。

這首詩主要描寫的是作者晚泊沙渚的所見所聞。
詩的首聯先點時間與地點:日暮片帆落,渡頭生暝煙;傍晚的時候,停船落帆,渡頭漸漸被晚煙籠罩。
僅從首聯中,我們并不能完全窺探到作者的具體心情,但是我們卻能能夠通過其中的內容感受到一種清幽的意味。
「日暮」在點出時間的同時,也為畫面涂抹讓了較為暗淡的色彩;「生暝煙」三個字進一步補充前一句的內容,并且為畫面增添了頗多的動感。
夕陽西下,渡頭暮煙裊繞,一葉扁舟緩緩停靠,無須特意說明,它已成為畫面中的重點。所以,細細說來,在首聯中,作者就已經將自己拉入了畫面,并且為后文的輸出奠定了基礎。
作者泊舟后,有什麼樣的舉動與所見?從接下來的頷聯開始,我們就可以得知詳細的內容:與鷗分渚泊,邀月共船眠;與白鷗同在這片沙渚停留,邀請明月與「我」同船共眠。
這一聯與孟浩然的「野曠天低樹,江清月近人」的意境有著相似之處,不過與孟詩相比,此詩的頷聯則又多了幾分淡泊與閑適之意。
作者分別選擇了「鷗」「月」這兩個物象進行描寫,其目的不僅是為了讓畫面顯得生動美麗,更重要的是為了體現出作者「置身于世外」的那種高尚情操。
「鷗」這一物象常常代表著與世無爭、回歸自然的心境。比如王維就曾寫過這樣兩句:野老與人爭席罷,海鷗何事更相疑;其中所要表達的,便是作者平淡質樸的情懷。所以作者在這里也是在借「鷗」鮮活意境,借「鷗」表明心志。
「邀月共船眠」更是通過對作者自在而眠的這一具體行為的刻畫,將他優雅、淡泊的形象體現出來。

頸聯繼續豐盈畫面:燈影漁舟外,湍聲客枕邊;在漁舟之外可以看到其他星星點點的燈光,在客枕邊聽到的,是湍急的流水聲。
和頷聯相比,頸聯的情感色彩顯然要沉重一些,不過它的畫面感依舊美麗。
前一句是是從視覺的角度做出的裁剪,后一句則是從聽覺的角度做出的裁剪。前一句于柔和中透露著孤寂之感,后一句則在中孤寂中透露著清寒之味。
為什麼說頸聯的情感色彩要沉重一些呢?關鍵原因就在于「客枕」這一詞的運用。從這一詞上,我們可以得知作者的游子身份,而當得知他的身份后,我們再去讀頸聯,其中的那味「沉重」也就自然很飽滿了。
作者盡管高風亮節,盡管淡泊無爭,但他畢竟身在他鄉,所以在淡泊之余,他還有更多的孤獨與寂寞,還有更多的關于思鄉的憂愁。這在尾聯中就體現得很充分:離懷正無奈,況復聽啼鵑;離家的心情很無奈,更何況反復聽到杜鵑的啼叫聲。
這首詩的情感是一步一步地緩慢推進的,一直到尾聯中,作者才將自己的思鄉之情鮮明地表達出來。
在野渡邊泊舟,在異鄉為客,作者本就是孤獨的,本就十分想念家鄉,而在這種情況下,他卻又聽到了杜鵑的啼叫,這就讓他更覺不安、更覺憂愁。
「杜鵑」之聲有「催歸」的意思,常被用來表達離愁別緒。所以尾聯借「杜鵑」的啼叫,很自然地將詩的情感推至[高·潮],讓我們在享受詩中的畫面所帶來的美感的同時,也被濃郁的憂傷所深深感染,達到了「言盡意永」的效果。

真山民的這首詩,語言自然,意境生動,的確很有唐詩的韻味,它能被詩家所推崇也算是實至名歸。
日暮杜鵑啼不歇,偏教客子起鄉思;各位看官,對于真山民的這首詩,你認為寫得如何?歡迎在評論區留言暢談。








